
小碎肉末
作者:李佳穎
出版社:洪範
出版日期:2008年06月05日
語言:繁體中文
ISBN:9789576742941
裝訂:平裝
李佳穎
一九七七年夏天生於台北。
交通大學外文系畢,科羅拉多大學語言學碩士。
〈遊 樂園〉獲一九九九年《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短篇小說首獎。
著有短篇小說集《不吠》、圖文書《47個流浪漢種》。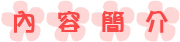
乾淨而迷幻、輕盈卻揪心的暢快小說
「李佳穎的文字乾淨冷靜像把刀子,又鋒利,又清澈,她把無滋無味的日常生活細細地切開來,於是讀者就見到那內部奇特的理路,無血,冷凝,又明明白白的是血肉。彷彿應該要痛,可是又不。寫出這樣的效果必須有非常精準的文字,寫人,寫景,也寫心。能夠自始至終都控制得這麼漂亮而不失手,每篇故事都完整而細緻,都剛剛好清清楚楚切在邊上,不賣弄技巧也不情緒失控,這樣優秀的作品近年實在少見,令人對新世代的作家產生莫大的期待。」
《小碎肉末》為小說家李佳穎的第二部短篇作品結集。
在「短篇小說」寫作上擁有獨特造詣的李佳穎,再次展現高超的敘事技巧與情境鋪陳能力。
十篇小說的主題,或大膽犀利,或淺易日常,卻同樣專注於人與人、人與生活物事間的種種交錯動念、動念後的歧異境遇。簡潔至精巧的情節中,往往帶有驚人的轉折力量,讀來餘韻悠長。而其低調、凝靜的文字口氣,引領著凌厲如電影運鏡的明快風格,散發出另一迷人的細緻張力。
The Case
費怡在廚房接到安珀電話時,手上正在煮義大利麵條。「妳現在可以說話嗎?」安珀問。
「嗯。」費怡說。另一端人聲吵雜,安珀英文說得又快又糊,費怡想安珀應該醉了,吐出的字被她在外頭特意浮誇的聲頻上下推開,費怡聽不清楚安珀在說什麼。但她知道安珀正問她是否可以說話,這已經是公式。再來安珀會說「妳一定不相信……」
「妳一定不相信這個,」安珀說:「嘿,費怡,費怡,妳在嗎?」
「我在聽。」費怡說:「嘿,安珀,妳可以說大聲一點嗎?」
「抱歉各位,這裡有位女士要去盥洗室!」安珀大聲地說,然後又是一陣抱歉聲,突然間嘈嚷的人聲不見了,像啪一聲轉熄一壺爐上沸水。費怡想像安珀關上了女廁門,話筒裡昏黃薰臭。
「費怡,喔,費怡、費怡、費怡 小卡奇剛打電話給我,他說要兩個敢玩又,唔,不怕死的女孩,妳聽到了我說的嗎?不怕死的女孩,嘶 其中一個得要是亞洲女孩,就一晚,妳知道對方給多少嗎?我的天啊!不可思議!」安珀大呼一口氣,然後給了她一個數字。
「小卡奇說他的份也要加倍,我叫他去幹自己。費怡,喔不,嗨,金,」安珀笑起來:「我叫小卡奇跟他們說妳叫金,他們要亞洲女孩,韓國女孩,我說妳叫金,安珀與金,哈。好姊妹。」
「什麼時候?」
「明天晚上。莫什麼時候會來?」
「禮拜五。」
「好,我得走了,喲呵!我的天啊!明天見。」
「明天見。」費怡說。
費怡把義大利麵瀝乾,打開微波爐拿出熱好的香菇炸醬,先倒一點炸醬在大圓玻璃盤上。她在廚房中央的流理台上做這些事,頂上的吊燈靜靜地發出色暈,熱燙炸醬吐出的煙霧一點一滴吃掉玻璃盤底下的暗光,她將義大利麵篩進圓盤,疊在已經盛入的炸醬上。剛煮好的義大利麵滑溜充滿彈性,她將幾根滑出盤緣的麵條撥入,把剩下的炸醬淋在上頭,她拿來湯匙將醬鋪勻,接著又加上叉子開始拌義大利麵。叉匙碰撞,攪動的黏稠肉燥與爽脆麵條發出微弱的啪答聲響,一小滴肉末濺到她的手腕內側,她舉起手舔去肉末。
她做的每一件事都讓她想到性。
費怡將盤子端到客廳配電視吃,深夜新聞剛開始,她專心地吃麵,但一則則新聞仍一字不漏鑽進她耳裡。陌生的單字扣著熟悉的單字,句子像一列列急駛的火車車廂,運來了戰爭、英勇的傷兵、醫療新制、法案攻防、連續殺人、車禍、圖書館館員閒暇時幫忙修理別人捐出的舊電腦送給貧窮社區的小學生。
費怡的英語每天都在進步,但是她話越來越少。她已經不再是一個外國人觀光客,她在這裡度過四季,鄰人也開始與她聊起天氣變化。初來乍到者能有的天真逐漸讓她感到難堪。費怡可以嫻熟地操縱語言,卻跟不上羅織在語言裡的性格,像一個語言的暴發戶,擁有越來越多的資產,卻越不知道要怎樣花用。
她想著剛才電話裡安珀說的一句話,安珀說「girls who don’t fear death」,不怕死的女孩,說完還開玩笑發出打顫的嘶嘶聲。這種事對她倆來說已見怪不怪:不怕死的女孩,嘶 事前客人的古怪要求在安珀嘴裡都成了玩笑的機會,辦事時約莫也是這模式。
費怡看過安珀將不知道是誰的大便抹在胸部上然後自己舔掉,那一次後來安珀把自己關在廁所裡整個晚上,誰知道她還吃了什麼。安珀金髮綠眼 據說傳自她百年前漂洋過海來到新大陸的愛爾蘭祖先 人也很熱情,對此安珀自稱為「本地人的天性」。費怡覺得無所謂,需要的話吃點大便也沒關係。她唯一要求是不見血,外傷不好隱藏。以她的身體來說,紅腫與淤青最少需要三天的時間才能勉強以遮瑕膏蓋起,她得計算前夫帶孩子來找她的時間。
不怕死的女孩,費怡想。不是頑皮,不是好色,不是虐,而是不怕死。從沒聽過這說法,還滿有創意的。費怡覺得自己似乎也不害怕真的被弄死,她倒希望誰來掛掉她,因為她自己太膽小。但其實那些人跟她一樣膽小,費怡知道他們,因為她也是他們。
傍晚安珀開車來接費怡。「嗨,金柏莉。」費怡打開車門時安珀說,說完自己咯咯咯笑起來。費怡跟著笑,像對安珀一直以來照顧她的報償。費怡不知道哪裡好笑,韓國人叫金,中國人都會功夫,那些關於刻板印象的笑話。不止安珀,許多顧客在辦事時也會來個一兩句,妳果然好緊啊,我的亞洲小寶貝,妳一定沒看過這麼大的屌吧。
是妳還是妳們?費怡想反正都一樣,越異之地界線越清明,日裔區,寮裔區,西裔區,非裔區,高級區,貧民區。也許對面前這人來說,她就是他一生中唯一接觸過的亞洲女孩,妳就是妳們。進屋來,把禁忌與尊嚴一起留在黑暗的大街上。費怡不能選擇只賣一樣,當她褪去衣物剩下細眼黑髮與貧乳,她也一併賣掉整個亞洲。
安珀稱每一次交易為「case」。這字費怡很早便認識,國中的英語教科書列為常用單字。費怡剛畢業時進入一家外商公司,裡頭的人也習慣混著用。老闆說,這個case很重要,要細心一點。同事說,這個月case多,趕case趕到快發瘋。
安珀說,This case saved my ass. I mean it. I am not kidding you. 這個case救了我的命,我是說真的,不是開玩笑。費怡知道安珀有許多問題,安珀有癮,還有個一樣有癮的男友,永遠都在需要case救命的狀態。安珀不了解費怡接case的原因,因為安珀進屋後什麼事都做得出來,私底下卻叫每一個顧客「變態」。不過她倆相識至此早過了問「為什麼」的階段,如今安珀已經不再問費怡為什麼要接case。
她們往市區開,安珀說,我們得換車。費怡點頭。
她們將車子停在市區一間超級市場外的停車場上。一台長型私家車來接她們,密閉的車廂裡她看不見窗外也看不見司機,車子很穩,但費怡感到坡度。安珀開了後座冰箱裡的香檳。喝一點吧,安珀說,上工前輕鬆一下。
她們幾乎快喝完一整瓶香檳,車子停了下來。開門的是一個穿著西裝的中年男子,費怡跟在安珀後面下車。一出車外發現天完全暗了,看不清楚遠方,聞起來是山上,野外露水的溼氣讓她起了小小的雞皮疙瘩,面前的建築像一幢古堡,四周打起的燈在黑夜裡描出房子的輪廓。費怡看到落地窗後簾幕透出昏黃光線,那簾幕動了一下,顯然有人正等待她們到來。小卡奇在收到安珀暗中撥出的鈴示後回電。「我們剛到。」安珀接起後對著話機說,壓低嗓子放慢速度,提醒顧客她們也是有影子的人。
中年男子與她們握手。費怡與安珀都握了,安珀一直趁那人不注意時睨著費怡偷笑。他向她們自我介紹為律師,艾倫.納利普先生,負責這案子所有法律相關的部分。說完後納利普先生帶她們走上石階,安珀轉頭誇張地對費怡做了一個「what?」的嘴型,費怡向安珀聳聳肩,她注意到納利普先生也用了「case」一字。
替他們三人開門的是一個紅髮女人。叫我莉莉絲,紅髮女人說,她穿著剪裁合身的套裝,費怡猜莉莉絲約莫六十歲,保養得非常好,要說四十來歲也可以。謝謝妳們來,莉莉絲說。
費怡以眼角掃向安珀,安珀不笑了,她看得出來安珀有點不安。屋裡很安靜,大廳挑高二樓,一進門便可以看到三件式的大型沙發,屋樑頂垂掛的吊燈與落地窗前的鋼琴。客廳沒有電視也沒有相片,刻意整理過地空曠。鋼琴底下的灰色長毛地毯裡一個鮮豔的東西抓住了費怡的視線。請跟我來,納利普先生說。他帶她們走過長廊,費怡遠遠發現原來是一顆桃紅色的卡通海灘球。那種小孩玩的,塑膠材質嘴吹的廉價海灘球,半洩了氣,軟攤在屋角鋼琴的腳踏板下。廊底有大理石製的半圓形扶手梯,她們跟著納利普先生上了二樓。費怡沿著冰涼的梯子繞,在最後一階上,她瞥見莉莉絲站在她們進門的地方,側過身去以指頭按壓自己眼角。
納利普先生在一扇門外停了下來。
「進門的桌上有袋文件,裡頭有詳細的工作指示與合約,以及一半的酬金。妳們得先讀完指示,在合約上簽名,才能開始工作。房間裡裝了攝影機,我會在另一個房間監看妳們,工作完成後我會把剩下的錢交給妳們。合約旁邊有支電話,有任何問題可按『1』與我對話。」納利普先生說話的口吻像個機器人,費怡覺得他對她們根本不感興趣。納利普先生在工作,她也在工作。費怡試著想像他們不工作的時候相遇會是什麼樣子。納利普先生說完便離開了,留她們兩個在那兒。
腳下還是一式的灰色長毛地毯,費怡著高跟鞋的腳板也感到溫暖。
「我不想這麼說,」安珀噓聲:「可是這地方真詭異。我寧願看到一群毒蟲律師或老同性戀女人的性派對。」安珀將耳朵貼向門板:「什麼都沒有。連個他媽的吸鼻子聲都沒有。」
費怡對安珀微笑,安珀給她一個「妳居然還笑得出來」的表情。費怡伸手開門,安珀跟在她後面。
一股淡緲的苦味隔離內外,費怡彷彿打開一扇白色大門。她經過門口放著牛皮紙袋的小桌,一步步走進房裡。安珀沒有跟上來,費怡聽見身後有紙袋開啟的窸窣聲音。空氣中還有一串微弱的響聲:嗶。嗶。費怡往房間中央走去。
一張大床,幾乎可容三個人平躺。床中央隆起一小丘。費怡正想走近時,安珀喊她。
「我們得先簽這些文件,」安珀看著手中的紙:「金!」安珀還是噓著聲音說話,房間裡太安靜,那味道讓她們不由自主捏著鼻息。費怡回到門口的小桌旁,安珀把其中一份文件交給她。「上面寫什麼?」費怡問。
「都是字!文件!我真不敢相信,」安珀搖著頭說:「他們應該高興今天來的不是貝嘉與琴。」費怡見過貝嘉幾次,貝嘉去年剛從波多黎各搭船來;琴則是個幾乎不說話的亞洲女人,因為她不說話,所以也沒人知道她從哪裡來。「上面寫什麼?」費怡問。
「所以我們必須提供舒適的性服務給床上那位處於疾病末期,括弧,非傳染性疾病,的先生,這是他生前預囑的一部分……等等等等……總之這位先生快掛了,無法性交,但還是想要爽一下,這位先生的生前預囑在律師與家人的見證下已經啟動,我們的行為與其所造成的結果都在法律保護之下……」安珀迅速地翻到最後一頁:「簽吧。」
「妳難道不想先看看『這位先生』嗎?」費怡對安珀說。
她們一起走向那張大床。除了進門小桌上的檯燈之外,室內只有床頭一盞立燈亮著,安珀的呼吸聲與空氣裡的嗶嗶聲響恰巧同拍。
她們就著立燈看見床上的人。那是一個穿著浴袍的老人,枯瘦的四肢從白棉袍底下掉出,老得讓人第一眼幾乎無法分辨他是男是女。費怡驚訝人老到一個地步,髮稀皮皺連性別都不見,她甚至覺得他可以是白種人也可以是黃種人。要不是呼吸器上均勻出現的薄霧與旁邊機器傳來穩定的嗶嗶聲,費怡甚至無法確定他是否還活著。九十歲?一百歲?或許更老?她不知道,但那些數字還有什麼差別呢?
安珀臉上出現嫌惡的表情,只有一瞬間。她顯然記得納利普先生在暗處的眼睛。「所以?」安珀看向費怡。
「簽嗎?」費怡問。
「為什麼不簽?」安珀說:「我看過更糟的。」
費怡不知道安珀口中所謂「更糟的」是什麼,她想起她們一起接過的case,也許安珀指的是那些她曾經抹在乳房上吃掉的稀屎。然而在費怡看來,沒有什麼比眼前這個皮囊還難了。這不是遊戲,不是無聊有趣的胡鬧實驗,不是窒息,綑綁,扮演,這甚至不是性;她可以想見接下來要發生的事不會有性那股獨特的,作態的歡愉,房裡的世界遠超出她的腦袋,費怡覺得自己正踏入一塊未知地。
費怡與安珀回到門口的小桌上,就著檯燈大略看了一下合約。她們提供的服務包括觸摸及親吻全身,動作必須小心輕柔。如果床邊的生理監視器上心電波律出現任何變化,或經監看人 納利普先生 認可後,服務即可終止。她們簽名的時候安珀低聲說:「噢,我恨有錢人。我恨他們。」
她們走回床邊,安珀開始褪去她的短洋裝。費怡不知道安珀這麼做有何意義,老人垮著薄可辨血管的眼皮,眼角混濁根本不見一物。費怡站在那兒看著安珀解開胸罩,雙腿微微互掩向前傾身以指頭勾下內褲,動作緩慢圓滑。安珀將脫下的內褲套在指尖上,輕輕舉起,優雅地放在床邊的地板上。費怡突然了解安珀在表演,安珀相信真正的顧客是黑牆裡監看的眼睛:納利普先生與莉莉絲與其他,他們。安珀相信這是有錢人的變態遊戲,安珀不問為什麼。安珀沒有看見莉莉絲最後一個表情。
費怡也不問為什麼,於是脫了衣服。
她們倆光著身子爬上那盒子般的三倍寬特製病床,床架因為重量增加嘎嘰叫了兩聲。費怡與安珀各臥老人一邊,她們的身體在被褥上沙沙移動,床邊生理監視器持續發出穩定的嗶聲。
「來吧,」安珀看著老人說:「先生。」
她們一起解下老人的浴袍腰帶,拉開兩片前襟。老人赤裸的身體攤在她們面前。不服老的老人費怡見過許多,然而枯朽至此她是第一次見到。眼前這副身體與死亡的關係就像煙與火,果與因一樣自然直覺。老人非常瘦,他的皮膚乾皺窘癟,貼著突出關節與骨頭彎曲的部分。他的喉頸宛如病雞的肉垂,薄皮折起堆積。費怡突然有個錯覺,彷彿他口鼻上的塑膠管子作用是將體內的氣體抽出,她想到市場真空包裝的肉骨,她與安珀沒人伸出手來。費怡眼神下移,磨蝕掉的肌理使老人的胸膛成了兩個失去支撐的肉袋,大小有點像剛發育的少女,然而質感蒼白粗糙,淡金色的細毛與淺褐斑點淹沒了老人的軀幹,她幾乎找不到那隱匿的,粉紅色接近肉色的乳頭。費怡的視線拂過老人清晰可見的隔膜,越過隆起的小腹,上頭肉紋崎嶇,彷彿一張可解的地圖。然後是老人的陽具。老人有一根與他此刻身體不成比例的陽具,頹軟垂向一旁。男人的陽具不使用時像個小老頭,床上這男人的身體卻老過了他的陽具。那陽具長在抽縐褶曲之間,反顯得光滑特出一如新物。陰部的毛髮比起軀幹上的要濃密一些,他乾柴棒似的雙腿與身體其他部位一樣佈滿了皺紋與淺褐色大大小小的斑。
費怡挺起上身,跪坐在老人身旁,拉起他懸薄的手,輕輕將嘴唇蓋在他的手背上。費怡開始舔起老人的前臂,一口一口,細白的沙塵皮末嚐來味苦,一股微酸的悶臭鑽入她的鼻翼,她才發現自己爬上床後便不自覺屏著鼻息以嘴呼吸。舌尖推過紋路轉澀,老人乾燥花駁的皮膚在眼前如旱地龜裂開,費怡得不時潤澤自己雙唇,親著手肘,膀子;安珀也一樣,她們各抓著老人一邊的臂膀像兩隻餓鬼,咂嘴泌出唾沫流得一身都是。
費怡領著老人的手掌覆蓋自己,繭的粗糙感在她乳房上清晰易辨,她感到自己身體的肉嫩。費怡的親吻行到手掌時發現老人靠她這邊的手少了兩根指頭,皆從第二指節斷起,斷面的疤糊了,長出皺紋,自然得彷彿指頭只是因疲勞而向內蜷起。費怡捧著老人斷指的手呆了半晌,一回神忽覺在這張床裡似乎動作停止時間也停止了,她趕緊傾身親吻老人胸膛。她親吻著,不著痕跡地貼上側臉,但耳裡除了嗶嗶的儀器響聲,便是安珀滋滋的吸吮聲。費怡慌張地看向老人嘴鼻,只覺塑膠罩管上的淡霧散去了,澄淨了。費怡轉頭看安珀,安珀伸過頸子來吻她,費怡記起安珀在表演。安珀認為顧客喜歡看她們親吻,她便吻了安珀「 一個虛假濡濕的吻 」 費怡才發現自己需要這樣的吻,安珀的表演之吻讓費怡感到安全一些。
表演是工作,表演是生活。老人捏出細眼黑髮與貧乳,說,讓這個case有韓國人,就有了韓國人;讓這個韓國女孩不怕死,就有了不怕死的韓國女孩。費怡無從得知老人是什麼人,她的疑惑沒有力量,老人無須對她交代。
費怡不怕死,這邊,那邊,她以為每一天她都更加接近自己的死亡,她不怕自己死去。一部好萊塢電影裡,芝加哥黑幫誤殺了人,之後整齣戲無論是黑道老大小弟或警察,所有人嘴裡都只剩下「那個日本人」。你有沒有幹掉那個日本人?誰叫你幹掉那個日本人?我他媽不小心幹掉一個日本人。日本人還沒死的時候有個名字,片子結束後費怡記不起來。在異鄉死去的人要死兩次,首先他死了,然後他的名字也死了,反之亦然。費怡以為自己不怕無聲無息死去,而這case不只。
她們移到老人股側,安珀伸出手握住老人的陽具,張開嘴湊上。費怡一面撫摸老人,一面看著這幅景象:安珀白滑的背脊橫在老人軀幹中間,兩人彷彿啦啦隊排列出人體T字。費怡低頭俯瞰安珀小小的金色髮旋馬達似地狂轉,手腕在困難的一套一弄中肌脈浮現,老人的陽具沒有反應。安珀在那團肉上使盡各式招法,許多安珀曾教她並眨眼笑說會「讓他們爽到認不得回家的路」的技巧都進入費怡眼裡,然而在這個case裡她倆成了無用性愛的暴發戶,那陽具在安珀嘴裡像一塊溫軟的麻糬。費怡看著安珀突然害怕起來,安珀鬆開嘴抬起頭,輕輕觸碰費怡的手。
停了。
費怡趕緊俯身含住,在性中有了想哭的感覺,費怡希望自己能像安珀一樣專心。她試著想像納利普先生在暗處的眼睛,但與納利普先生的短暫交談讓她直覺他並不樂於監視這個case,也許他會在隔壁房間的螢幕前因勃起而感到屈憤羞恥,也許老人的身體令他心驚,他正轉開頭去。費怡試著想像莉莉絲的眼睛,卻想起她按著眼角別過臉的模樣。費怡感到老人更皺了,顏色更深了,費怡伏著的乳頭輕輕磨蹭老人的腿側,溫度也暗下來。韓國女孩。為什麼?費怡望向床頭,老人雙目合攏的頭顱看起來像一個蓋得緊緊的,遺失鑰匙的舊鐵盒:你曾經對韓國女孩有秘密的想像?你曾經愛上韓國女孩?曾經有韓國女孩傷了你的心?還是你曾經參加戰爭,在遙遠的東方有著不為人知的秘密?
費怡的嘴裡滿是安珀留下的黏涼唾沫,有時候那肉在她舌抱裡抽跳一下,但馬上又發現是錯覺。費怡想著口中這老人,無可避免地在自己有限的世界裡尋找立下這般生前預囑的邏輯,因此費怡感到惱怒:多麼卑鄙!這是一個無行動能力的傢伙,行使他在還能行動時所預支的一點能力,他希望她掛掉他,他才是她的妓女 這一秒鐘費怡竟嫉妒起這老人,舉止散漫分神,她不想稱他的意。但她不敢完全停下來,床上的時間得靠她的動作啟動。快過去吧,一想到這兒她又賣力地舔著,希望那嗶嗶聲能突然改變節奏。費怡在兩思緒間來回,時而欲振時而乏力,狗一般叼塊冷肉無止境地五十公尺折返跑……多久過去了,費怡的精神極度疲累,一眨眼有淚順著輪廓滑下。
費怡已經很久沒有流淚,雖然她無時無刻不想哭泣。孩子出生時她學會他哭了要抱他、餵他、或是替他換上乾淨的尿布。但有那麼些時候,當乾爽清潔的孩子在她懷裡聲嘶力竭地哭號,吐著小舌閃躲她的乳房,費怡只能瞪著他毛軟的頭顱。費怡覺得很抱歉:眼前這個小小的人與他小小的鐵盒,他的需要已大於三,無論他還需要什麼,他需要被瞭解,哭泣是他唯一的語言。
如今費怡能說大於三種的語言,包括哭泣,然而幾乎再也沒有人因為無法瞭解她而感到抱歉了,感到抱歉的人大都自以為瞭解了某些事情。但情況是,許多時候連她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要說某些話,做某些決定;為什麼在這裡,為什麼哭泣?
床上的老人長出了皺褶幾乎覆去身上原有標記,如同一張新的身分,他沒有辯解也沒有批評,不愛慕也不輕薄;不高潮也不忍耐,不推延也不努力。僅存的線索化成文字躺在門口的小桌上,他躺在床裡一聲不吭。為什麼她仍要對他感到好奇?憑什麼?
安珀見費怡掉淚,趕忙倚身摩娑她的臉輕聲說:「喔,寶貝,喔,費怡,喔甜心……」一絲不掛的安珀能給費怡的仍是一個吻 「 卻是個輕盈憐憫的吻 」 費怡害怕得幾乎要躲開,但已經來不及,她來回奔跑而旋緊的心終於在那一瞬為了幾秒後的墜落而騰空,安珀不懂卻溫暖的唇像一方包容的屍布,緩緩將費怡尚未出口的話全蓋了起來……
忽地,一絲細線穿透她倆齒間,姆姆嗚嗚像扼著頸子就要斷氣的人,費怡睜大眼睛看見安珀觸電般從她臉前鬆口,一後退彷彿「玻!」一聲拔開水槽底的橡皮塞。那一刻,費怡聽見自己唇縫嘩啦啦洩出簡單的旋律。起初調子稀薄遙遠有如從黑牆裡傳來,漸漸地,費怡嘴裡抽芽的音符覆去了機器的嗶嗶聲,覆去了安珀的滋滋親吻,覆去了老人難辨的心跳,也覆去了她的咒詛。費怡以為自己在哭號,但那聲音聽起來單調反覆而快樂,像一支遺詞的童謠。
黑色私家車載她們回到市區超級市場的停車坪,在私家車上費怡與安珀沒有交談。那車走遠後,她們坐上安珀的車,車子發動,儀表板上的霓虹時鐘亮起,前後不過幾個小時。
「妳還好吧?」安珀斜倚在方向盤上有點擔心地望著費怡:「妳剛才嚇到我了。」
「沒事,」費怡搖搖頭:「對不起。」
超級市場外,一個婦人將最後一袋雜貨從手推車中拿出來放進後車廂裡。牛奶,紙巾,麵包。婦人寬鬆的淺色連身裙在夜裡隨風飄搖,像一朵癲狂的花蕊。婦人離開了。她們坐在暗黑的前座,沒有人接話,彷彿剛才簡短的問答值得一陣沉思。突然安珀想通什麼似地 「 或放棄了 」 吐了一口氣,車子開始向後移動。費怡從照後鏡裡看見白熱路燈下,幾台超級市場的紅色手推車零星散置在幕黑地曠的停車場上。費怡望著那些小小的紅色手推車。
「安珀,妳看見了嗎?」
「看見什麼?」
「扁掉的塑膠海灘球。」
「哪裡?」
「桃紅色的。在那房子客廳的鋼琴底下。」
「喔,那個,不是海灘球吧?看起來是某種噁心的性玩具。」
「是嗎?」
「肯定是。一屋子的變態,」安珀說:「我接過最怪的case之一。看看那個老人,天吶,他真老,我沒見過比他更老的人了。我真懷疑他到底知不知道今晚我們在那裡口水流得他全身都是。我不懂他們幹嘛一定要韓國人,對那位先生來說 妳知道我的意思,韓國人,越南人,日本人,愛爾蘭人,泰國人……」安珀轉過頭來:「有什麼差別?」
費怡本想告訴安珀一個她小時候的故事,可童年的小海灘球隨著安珀的句尾漂遠了。費怡按下窗戶,讓超級市場廚房的油炸味道飄進車內,她曾經在許多不同的地方聞過煎炸食物的味道,這裡,那裡,費怡從不慶幸自己屬於任何地方。但是 費怡準備告訴安珀,安珀將不懂也不問為什麼 今晚那幢房子 費怡想起莉莉絲的手勢以及老人透明的呼吸,她感到自己的臉柔和下來,她有了一點重量 在今晚的case裡,她很高興自己不是一個不怕死的韓國女孩。
這些故事有的以美國為背景,有的是台灣的城鎮~~
但是,貫徹其中的情緒和氛圍非常一致~~
這書裡瀰漫著「存在卻不在場」、「在場卻不存在」的清醒微病感,一切懸於一線,又恍惚又緊繃~~
- Feb 27 Sat 2010 18:41
小碎肉末 作者:李佳穎
close
全站熱搜
 留言列表
留言列表
發表留言


 留言列表
留言列表
